近日,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彭璐珞在《中国组织人事报》整版发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富民厚生 以利四方》,展现湖大商学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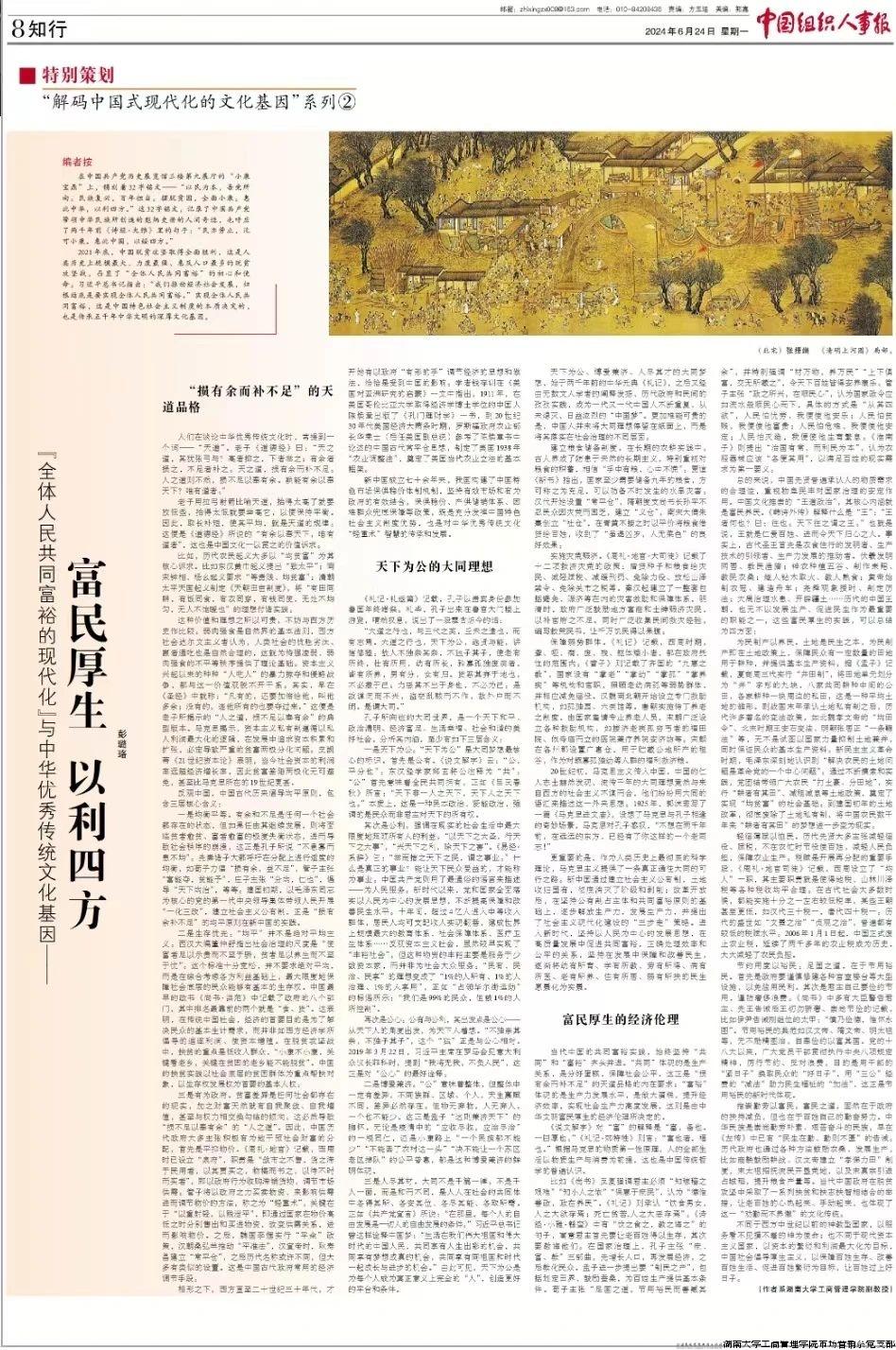
全文如下: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三楼第九展厅的“小康宝鼎”上,镌刻着32字铭文——“以民为本,吾党所向。民族复兴,百年担当。摆脱贫困,全面小康。惠此中华,以利四方。”这32字铭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也呼应了两千年前《诗经·大雅》里的句子:“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2021年底,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凸显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也是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文化基因。
“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品格
人们在谈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常提到一个词——“天道”。老子《道德经》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用拉弓射箭比喻天道,抬得太高了就要放低些,抬得太低就要举高它,以便保持平衡。因此,取长补短,使其平均,就是天道的规律。这便是《道德经》所说的“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也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
比如,历代农民起义大多以“均贫富”为其核心诉求。比如东汉黄巾起义提出“致太平”;南宋钟相、杨幺起义要求“等贵贱、均贫富”;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制定《天朝田亩制度》,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的理想付诸实践。
这种价值和理想之所以可贵,不妨与西方历史作比较。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赢者通吃也是自然合理的,这就为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种种“人吃人”的暴力掠夺和侵略战争,都与这一价值观脱不开干系。其实,早在《圣经》中就称:“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便是老子所揭示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典型版本。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遵循以私人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在发展中追求资本积累和扩张,必定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表明,当今社会资本的利润率远超经济增长率,因此贫富差距两极化无可避免,甚至比马克思所在的19世纪更甚。
反观中国,中国古代历来倡导均平原则,包含三层核心含义:
一是均衡平等。有余和不足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状态,但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则将面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极度失衡状态,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这正是孔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先秦诸子大都呼吁在分配上进行适度的均衡,如荀子力倡“损有余,益不足”,管子主张“富能夺,贫能予”,庄子主张“分均,仁也”,倡导“天下均治”,等等。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开展“一化三改”,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正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均平原则在新中国的实践。
二是生存优先。“均平”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西汉大儒董仲舒指出社会治理的尺度是“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这个标准十分宽松,并不要求绝对平均,而是在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底层的民众能够有基本的生存权。中国最早的政书《尚书·洪范》中记载了政府的八个部门,其中排名最靠前的两个就是“食、货”。这表明,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民众的基本生计需求,而并非如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追逐利润、使资本增殖。在脱贫攻坚战中,扶贫的重点是低收入群众,“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中国的扶贫实践以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为重点帮扶对象,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
三是有为政府。贫富差异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现实,加之财富天然就有自我聚敛、自我增值,甚至与权力相交换勾结的倾向,这必然导致“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因此,中国历代政府大多主张积极有为地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首先是平抑物价。《周礼·地官》记载,西周时已设立“泉府”,职责是“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即以政府行为收购滞销货物,调节市场供需。管子将以政府之力买卖物资、来影响供需进而调节物价的方法,称之为“轻重术”,关键在于“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即通过国家在物价高低之时分别售出和买进物资,改变供需关系,进而影响物价。之后,魏国李悝实行“平籴”政策,汉朝桑弘羊推动“平准法”,汉宣帝时,耿寿昌建立“常平仓”,之后历代名称或许不同,但大多有类似的设置。这是中国古代政府常用的经济调节手段。
相形之下,西方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有以政府“有形的手”调节经济的思想和做法,恰恰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学者钱存训在《美国对亚洲研究的启蒙》一文中指出,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陈焕章出版了《孔门理财学》一书,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农业部长华莱士(后任美国副总统)参考了陈焕章书中论述的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制定了美国1938年“农业调整法”,奠定了美国当代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我国构建了中国特色市场保供稳价体制机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保供稳价、产供储销体系、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等政策,既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轻重术”智慧的传承和发展。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以贵宾身份参加鲁国年终蜡祭。礼毕,孔子出来在鲁宫大门楼上游览,喟然叹息,说出了一段震古烁今的话: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是一个天下和平、政治清明、经济富足、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的美好社会,分析其内涵,至少有如下三层含义:
一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大同梦想最核心的标识。首先是公有。《说文解字》云:“公,平分也”。东汉经学家郑玄将公注释为“共”。“公”首先意味着全民共同拥有,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本质上,这是一种民本政治、贤能政治,强调的是民众而非君主对天下的所有权。
其次是公利。强调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最大限度地照顾所有人的利益,“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易经·系辞》曰:“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什么是真正的事业?能让天下民众受益的,才能称为事业。中国共产党则用了最通俗的语言来描述——为人民服务。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十年间,超过4亿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翻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反观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较早实现了“丰裕社会”,但这种物资的丰裕主要是服务于少数资本家,而并非为社会大众服务。“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变成了“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所示:“我们是99%的民众,但被1%的人所控制”。
再次是公心。公有与公利,其出发点是公心——从天下人的角度出发,为天下人着想。“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个“独”正是与公心相对。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提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正是对“公心”的最好诠释。
二是博爱兼济。“公”意味着整体,但整体中一定有差异,不同族群、区域、个人,天生禀赋不同,差异必然存在。但物无弃物,人无弃人,一个也不能少。这正是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无论是疫情中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一视同仁,还是小康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的公平普惠,都是这种博爱兼济的鲜明体现。
三是人尽其才。大同不是千篇一律,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和而不同,是人人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诠释中国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由此可见,天下为公是为每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完全的“人”,创造更好的平台和条件。
天下为公、博爱兼济、人尽其才的大同梦想,始于两千年前的中华元典《礼记》,之后又经由无数文人学者的阐释发扬、历代政府和民间的孜孜实践,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重复、从未熄灭、日益浓烈的“中国梦”。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人并未将大同理想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将其落实在社会治理的不同层面。
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古人养成了防患于未然的长期主义,特别重视对粮食的积蓄,相信“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贾谊《新书》指出,国家至少需要储备九年的粮食,方可称之为充足,可以防备不时发生的水旱灾害。汉代开始设置“常平仓”,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不忍民众因灾荒而困乏,建立“义仓”,南宋大儒朱熹创立“社仓”,在青黄不接之时以平价将粮食借贷给百姓,收到了“虽遇凶岁,人无菜色”的良好效果。
实施灾荒赈济。《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救济灾荒的政策:借贷种子和粮食给灾民、减轻赋税、减缓刑罚、免除力役、放松山泽禁令、免除关市之税等。秦汉起建立了一整套包括蠲免、赈济等在内的灾害救助和保障体系,明清时,政府广泛鼓励地方富商和士绅赈济灾民,以补官府之不足。同时广泛收集民间救灾经验,编写救荒民书,让千万饥民得以果腹。
保障弱势群体。《礼记》记载,西周时期,聋、哑、瘸、废、残、躯体矮小者,都在政府抚恤的范围内。《管子》则记载了齐国的“九惠之教”,国家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等机构和官职,照顾老幼病孤等弱势群体,并相应减免徭役。汉魏南北朝开始设立专门救助机构,如孤独园、六疾馆等。唐朝实施侍丁养老之制度,由国家雇请专业养老人员,宋朝广泛设立各种救助机构,如接济老疾孤穷丐者的福田院、依寺庙而立的医院兼疗养院安济坊等。宋朝在各州郡设置广惠仓,用于贮藏公地所产的租谷,作为对鳏寡孤独幼等人群的福利救济粮。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仁人志士赫然发现,流传千年的大同理想竟然与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不谋而合,他们纷纷用大同的语汇来描述这一外来思想。1925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设想了马克思与孔子相逢的奇妙场景,马克思对孔子感叹,“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
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真正通往大同的可行之路。新中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收归国有,彻底消灭了阶级和剥削;改革开放后,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原则的基础上,逐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策略。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渐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愿景化为实景。
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
当代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始终坚持“共同”和“富裕”齐头并进。“共同”体现的是生产关系,是分好蛋糕,保障社会公平,这正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品格的内在要求;“富裕”体现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做大蛋糕,提升经济效率,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这则是由中华文明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所决定的。
《说文解字》对“富”的解释是“富,备也。一曰厚也。”《礼记·郊特牲》则言:“富也者,福也。”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人的全部生活以物质生产与消费为前提,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认识。
比如《尚书》反复强调君主必须“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保惠于庶民”,认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礼记》则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诗经·小雅·緜蛮》中有“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的句子,寓意君主首先要让老百姓得以生存,其次要教诲他们。在国家治理上,孔子主张“庶、富、教”三部曲,先增长人口,再发展经济,之后教化民众。孟子进一步提出要“制民之产”,包括划定田界、鼓励蚕桑,为百姓生产提供基本条件。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并特别强调“材万物,养万民”“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令天下百姓皆得安养康乐。管子主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认为国家政令应如流水般顺民心而下,具体的方式是“从其四欲”,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淮南子》则提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认为衣服器械应该“各便其用”,以满足百姓的现实需求为第一要义。
总的来说,中国先贤普遍承认人的物质需求的合理性,重视物阜民丰对国家治理的安定作用。中国文化推崇的“王道政治”,其核心内涵就是富民养民。《韩诗外传》解释什么是“王”:“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也就是说,王就是仁爱百姓、进而令天下归心之人。事实上,古代圣王首先是衣食住行的发明者、生产技术的引领者、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伏羲发明网罟、教民渔猎;神农种植五谷、制作耒耜、教民农桑;燧人钻木取火、教人熟食;黄帝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尧舜观象授时、制定历法;大禹治理水患、开辟疆土……历代的中国王朝,也无不以发展生产、促进民生作为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这些富民厚生的实践,可以总结为四方面:
为民制产以养民。土地是民生之本,为民制产即在土地政策上,保障民众有一定数量的田地用于耕种,并提供基本生产资料。据《孟子》记载,夏商周三代实行“井田制”,将田地单元划分为“井”字形的九块,八家共同耕种中间的公田,各家耕种一块周边的私田,这是一种平均土地的雏形。到战国末年承认土地私有制之后,历代许多著名的变法政策,如北魏孝文帝的“均田令”、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等,无不是试图以国家力量抑制土地兼并,同时保证民众的基本生产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通过不断摸索和实践,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等土地政策,奠定了实现“均贫富”的社会基础。到建国初年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进一步变为现实。
轻徭薄赋以恤民。历代先贤大多主张减轻徭役、赋税,不在农忙时节役使百姓,减轻人民负担,保障农业生产。税赋是开展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西周设立了“均人”一职,其主要职责就是使得地税、山林川泽税等各种税收均平合理。在古代社会大多数时候,都能实施十分之一左右较低税率,某些王朝甚至更低,如汉代三十税一,唐代四十税一。历代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普遍都有较低的税赋水平。2006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废止农业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节约用度以裕民。足国之道,在于节用裕民。首先是政府要谨慎修建各种宫室楼台等大型设施,以免滥用民利。其次是君主自己要俭约节用,谨防奢侈浪费。《尚书》中多有大臣警告君主、先王告诫后王切勿骄奢、崇尚节俭的记载,比如伊尹告诫刚继位的太甲:“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节用裕民的典范如汉文帝、隋文帝、明太祖等,无不励精图治,自奉俭约以富其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目的是用干部的“紧日子”换取民众的“好日子”,用“三公”经费的“减法”助力民生福祉的“加法”,这正是节用裕民的新时代体现。
推崇勤劳以富民。富民之道,固然在于政府的扶持减负,但也在于百姓自己的勤奋努力。中华民族是崇尚勤劳朴素、艰苦奋斗的民族,早在《左传》中已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告诫。历代政府也通过各种方法鼓励农桑、发展生产,比如商鞅鼓励耕战、汉文帝建立“孝悌力田”制度,宋太祖招抚流民开垦荒地,以及宋真宗引进占城稻,提升粮食产量等。当代中国政府在脱贫攻坚中采取了一系列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举措,让老百姓的心热起来、手动起来,也体现了这一“劝勤而不养懒”的文化传统。
不同于西方中世纪以前的神教型国家,以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为使命;也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的繁衍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中国社会倡导厚生主义,以保障百姓生存、改善百姓生活、促进百姓繁衍为目标,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我要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全部评论 (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