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道炫:垂直和扁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构造
群众路线的提出,是中共抗战时期的创造,又有着深远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渊源。从苏俄革命开始,革命就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更是思想文化的全面翻覆。抗战时期中共的论述是:“要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智慧,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与依靠群众并不矛盾,但两者又不能混淆,要让群众知道我们的任务,我们才能和群众一道工作。” 也就是说,中共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统治者,而应该教育和提高民众,共同完成政治任务和目标。正因此,抗战时期中共既建立了直接下探到基层的垂直的权力运作体系,又开发了一套扁平型的政治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垂直和扁平相互补充的政治运作体系,将中共和绝大多数政治力量区别开来,不仅使中共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
扁平化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起初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出现的背景在于:“支撑科层制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导致其有效性的基础不断流失,扁平化作为突破科层制的结构模式,在企业管理领域取得广泛成功。”对于企业扁平化组织的核心原则,有研究者概括为:“围绕交叉职能核心流程而不是围绕任务或者职能进行组织”;“使团队而不是个体成为组织设计和实施的基石”;“与客户和供应商融为一体”;“利用信息技术帮助人们实现目标并把价值主张传递给顾客”;“促进多技能化、提高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灵活应对团队工作中出现的新挑战的能力”;“建立一种开放、合作、协调的企业文化,一种既聚焦持续性发展又重视对员工的授权、责任感和生活的企业文化”。团队、沟通、教育、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控制成为扁平化结构的核心概念。由于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盖伊·彼得斯及澳大利亚学者欧文·休斯等的努力,扁平化理念也应用于公共管理及官僚制度的考察。
有趣的是,抗战期间中共的政治构造中,可以看到和这个后来出现的概念相似的理念,只是抗战时期中共对扁平化结构的运用,更多体现于和组织相辅助的政治文化当中。关于中共扁平型政治文化的建立,既有研究阐述较少,学者祝灵君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共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大都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党组织中的官僚制,希望军队和政党组织扁平化,这样可以使政党对社会事务快速反应,另一方面也与中共所追求的平等精神保持一致。”引进扁平化概念观察中共政治的特征,很具启发意义。
扁平化和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群众路线若相契合。1943年,毛泽东对群众路线做了最早的集中阐述,做出规定性的概括: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件),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提法,很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定位.群众路线体现着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概括而言,即刘少奇阐明的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后来扁平化理念倡导的团队、合作、教育、情感沟通,都可在群众路线中找到脉络。群众路线强调打破干部和群众间的界限,减少沟通的层级,让干部和群众间形成同心圆而不是等级分明的阶梯式关系,这都和扁平化理念接近。扁平化理念倡导的团队、集体既是共产主义运动天然的选项,也是以集体、平等为取向的群众路线的基石。
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抗战时期中共系统化的政治文化的关键。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颇能代表中共政治文化的三大优良作风为例,紧密联系群众和群众路线的关系自不待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事实上其思考源头和落实践行也不能离开群众,也都源于群众路线的认知基础。群众路线的落实,最重要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眼睛向下看,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关心他们就不能代表他们。”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有效解决了控制力的问题,却带来了官僚主义的担心,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当程度寄托于群众路线。通过群众路线政治文化的树立,辅之以政治化的群众运动,可望打破等级化的官僚政治,塑造平等的同志式情感,以此保持和群众的水平关系:“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
应该指出的是,战时根据地垂直下探的权力体系和水平式的群众路线的政治文化,看似两个路向,其实相辅相成。正是有了垂直下探的权力体系,有了深入到民众之中的干部体系,群众路线的推进才有了更为有力的载体,才能避免传统亲民政治高高在上无从落实的困境。垂直下探的权力体系,固然有可能造成等级森严的控制体系,却也可能形成政治权力水平扩展的基础,在基层尤其如此。当中共强调群众路线时,通过权力下探形成的基层干部体系,迅速担负起构建同心圆的责任,这或许是权力下探时并未预想到的另一重功能。如果注意到中共的运作系统通常都环环相扣,这样的预料之外或也在情理之中。
二
群众路线、水平融合,落实的关键在干部。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的干部考核和评价体系,促进民众和干部的结合。模范干部的标准是:“能完成任务,不行政命令;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事事领头干;不贪污,不浪费,不流氓习气与浪漫习气。”这一标准不是摆设,而是落实到具体的数据当中:“村干部有100个群众真正拥护,县干部有1000个群众真正拥护。” 这个标准既体现中共数字化管理的要求,也符合干部要得到群众授权的思路。刘少奇有个想法:“派干部作县长,先不派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工作做好了,有了信仰,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 起码就理论上言,群众关系成为认定模范干部最重要的标准,“吃窝头小米,背行李跑路,穿老百姓的衣服到敌区工作”,几乎成为战时中共干部的常态。老百姓感到“现在的政府,不像个政府,像个群众团体”。对于一个以群众路线为取向的政治力量言,这样的评判毋宁说是极大的褒奖。相对于垂直的制度化的权力下探,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扁平型政治文化更是党和群众相互创造的过程,是变化、形成着的充满活力的政治实践,当年,群众运动又是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载体。
对群众运动的强调几乎和中共降生同步,中共二大起就确立组建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的组织原则。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下达指示信,首次提到“群众路线”,要求红军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 。抗战期间,由于获得相对稳固的独立发展空间,群众运动呈不断落实和推广之势。当时的劳模运动很能代表中共以群众运动拉进与群众距离的路径。1940年代,根据地广泛开展劳模运动,劳模不是干部,从群众中产生,是群众的代表,但他们作为群众中的脱颖而出者,又和一般群众拉开距离,可望成为“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如果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共对自己干部的要求,代表党向群众不断靠拢的努力;那么劳模则从另一面努力,作为连接中共和群众的纽带,带领群众向党靠拢。通过这样群众性的劳模运动,中共和群众间形成良性的相互靠拢的互动关系。来自国统区的记者赵超构观察到:“劳动英雄制度的最初动机,本只是提高劳动效率,但是现在的成果却已大大的超过了这最初的目的,一如我们看到,这些英雄不仅成为群众学习的模范,他们并成了共产党和民众之间的桥梁。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得边区民众和共产党执政之下而仍能发生平等的感觉。……相当的提高了农工的自尊心,而使他们乐于追随着共产党的政策。”
开展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曾经论述:
要把群众从和平的、散漫的、蒙昧的情况中转变过来,要他拿起枪来打仗,不怕流血不怕死人,而且还要各地大家都齐心一致,真不是桩容易的事情。……群众在思想上情绪上的复杂,人心不齐,旧势力统治的阻碍,文化低落,见闻狭小,传统成见的束缚与顾虑之多(保守,认命、自私、多疑,懦弱、家庭生活之牵累),这些事都成为发动群众的障碍,决不是抽象的想象所能知道。
黄敬道出了群众的自利自保本能,这是面对群众时不能不正视的现实。要真正让群众起来,必须在实践中教育群众、引导群众,让他们“了解到解决切身的事要和大家联合的必要。要使他们在大家为切身[利益]斗争中把眼界放宽了”。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发动群众要照顾群众切身利益,启发群众的自觉自主意识,让他们体会到自身利益和党的利益一致;二是在切身利益的斗争中放宽群众的眼界,使之不再完全陷于个人利益。因此,群众路线不仅要求党的干部向群众靠拢,还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要求,形成党和群众正相关的双向运动。实际上,共产主义运动都强调要面向群众,中共群众路线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仅强调到群众中去,还强调从群众中来,而这里的群众又是动态的,有群众的自觉自动,还有群众的教育提高,仅仅强调前者,有可能流于民粹,只强调后者,又有精英主义的风险。
共产党是先锋队的组织,当然负有领导和教育群众的责任,但是一旦站到领导和教育者的地位,党和群众的水平关系就岌岌可危,先锋队和群众似乎存在天然冲突。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是:教育和领导群众不在群众之外,而在群众之中。教育和领导群众之前,首先是向群众学习:
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革命实践的要求,也是共产党人认识论的基础。背后隐含的,有中共希望形成的干部与群众间情感上的共鸣、关系上的水平互动、地位上的可互换性等一系列富有张力的内容。
三
任何政治理念落地都有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越是精致的理想,落实的困难越大,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果一马平川,群众路线实施也就太过轻而易举。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在调查中发现:
张日福,一个63岁的老农,土地革命后到现在一共被绑了5次。第一次因儿子开会不到被绑,第二次因儿子躲避兵役跑到宜川被绑,第三次因与农民会长吵嘴被绑,第四次与部队吵嘴被绑,最近一次因运盐路费少出5元,被区上绑了一天,结果罚了50元。
我们和区乡的干部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不绑不行。我们提出施政纲领来和他们讨论,支部书记说照施政纲领来什么也办不通。
作家王林也在日记中讲到:石友三的军队拿病骡子强换老百姓的好马,还要老百姓给军队钱,换完没几天,马死了,军队又找上门要回换的骡子,“此事嚷动全村,所有老幼皆议论纷纷,最后最普遍的结论是:‘上哪里说理去呀,他又不是八路!’……百姓谈话常有这口头语:‘八路军也有坏的,国军也有好的。’”这一段特别具有生活的气息,石友三军队强换骡子招致的议论以及村民自然而然将之与八路军对比,都体现了当年军民关系的实态,而另外材料说到的,民众“觉得并且常常说出来:‘八路军好一点’”,其中的褒贬大体也是当时真实状况的体现。
追求至善尽美的中共,对民众带有限制条件的褒扬或许不能完全满意,黄敬就批评一些人和国民党比,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强调:“绝不能以比专员好一些为满足,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不过,从另一面说,当年的历史运动中,“好一点”透出的选择对历史进程可能产生的影响确也不可小觑。战争时期,很多事无法尽善尽美,作家高鲁的日记记载一个管理部队后勤的司务长的故事:
他和管理员押运十几大袋小米由白文到寨上,黄昏牛车回去了,这时他没动员着牲口,第二天队伍就要出发了,他可着急坏了,对管理员说:“粮食怎么搞得动,大车昨天放回去了,今天牲口也搞不出。”……管理员说:“粮食搞不走砍你的头!”“谁说砍我的头?”……他们俩就大声地吵起来,不一会从上面下来一辆大车,管理员就大声叫:“喂,老乡,喂老乡。”老乡一听就知道不对,赶快走,他就跑过去把大车硬拉来才算了事。
高鲁追问:“到战斗时是饿肚子要紧还是不犯纪律要紧呢?”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不过仔细想,在当年的政治力量中,大概只有共产党人才会有这样的追问,这何尝不是群众路线努力的结果。
当中共努力贴近群众时,常常会发现,随着获得权力的增长,群众的权力意识也在不断增长中。干部们抱怨:“现在的社会不同了,要在过去国民党下面,要什么老百姓还敢说个‘不’字?现在就不行,下农村说得不对,老百姓还敢骂人。”中共用权力下探强化了管控力,又用群众路线保持政权和民众间的权力博弈,一旦权力博弈开始,进进退退就成常态,有人会利用政治力量的善意钻空子:“我们开始下去花了十几万帮助老百姓开荒、买工具、买猪鸡等东西,但以后有人提出过份的要求,比如有一个商人他生活还不错,他要我们帮助他开荒,他好坐享福利,这是迁就落后,培养二流子,假使不能好好的注意就受了他的欺骗。”满怀善意接近群众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开始下去为了和老百姓关系搞好,就拜干妈干姐。结果把关系弄乱了,长辈搞成晚辈。同时拜干妈其他老百姓吃醋。搞好了一个,搞坏了十个,不能普遍的把关系搞好。同时发生纠纷的时候他可以利用干女儿的面子说情,比如这次发生纠纷他就说‘你是我的干女儿,你应该替我说话’。”
权力意识滋长带来的讲价钱、搭便车、占便宜等问题,让基层工作者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权力运用从单向变成博弈,干部和民众形成水平关系,由此带来的亲近感、信任感,是中共获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八路军干部刘荣写道:“下午推碾子。老乡说:‘从前当官的人都见不到,现在你们八路军当官的又说又笑,还推碾子拉磨,真是少见呀。’”一个向来缺乏平等和公正基础的社会,群众路线带来的新式干群关系,足以让民众心服口服,这是已经拥有权力意识的后人难以想象的。
战时中共既在根据地完成了空前严密的垂直权力体系,又构建了群众路线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垂直下探的权力体系代表组织硬的一面,群众路线则代表文化软的一面。党超然的垂直领导和水平的情感互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共对这两者的运用,可以说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巅峰。应该说,由于统一战线的范导及严峻的生存要求,抗战时期的群众路线贯彻可谓成功,成为中共政治构造的一个神来之笔,也因此沉淀为中共革命的重要政治和历史资源之一。日本人承认:“对于在民众里长下深根,且能巧妙掌握民心之共产党军,想把他和一般民众分离判别,实是困难事情。”这可以说是对群众路线政治文化实际成效的最好解读。当然,由于在党的领导和发挥群众自觉性间把握綦难,群众路线的理解和执行也不是没有难题,如何有效运用这一政治原则,推进政治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原载于第1575期《北大校报》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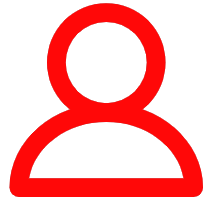


我要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全部评论 (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