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教授梁立基:从海外“孤儿”到民间大使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梁立基,1927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51年进入北大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以及东方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梁立基
海外血雨腥风中的青少年时代
海德格尔说过,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无法选择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国家和什么家庭,但来到世界之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
我是1927年来到这个世界的,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和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我的幼年和青年是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八月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度过的。
我的父亲梁尚琼是一位爱国侨领,他从小就教育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家客厅里挂的横幅是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我在万隆中华学校念书时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老师经常讲抗战的故事。我还特别喜欢唱抗战歌曲,记得每次唱《松花江上》和《八百壮士》时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决心要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一生。
“七七”事变后,在荷兰殖民统治下,万隆的爱国华侨只能以赈灾的名义进行募捐来大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当时万隆成立了华侨慈善委员会,我父亲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也想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救国做点儿事。所以一到周末,我便去慈善委员会的财务处领取募捐箱,沿街号召来往行人募捐,中午募捐完后便把募捐箱交还给财务处,当面点清我当天募到的钱数,然后写上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因为这意味着我也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自己小小的贡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很快伸向东南亚。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面临战争的直接威胁,城里人纷纷迁往郊外避难。我家迁到郊区山下公路旁的一间房子,在房屋后挖了一个防空洞,一听到空袭警报声,全家人便迅速躲到里面,蜷缩着一动不动。
不久,整个印度尼西亚便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万隆市沦陷不到一个月,我的家便惨遭浩劫。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把我父亲从睡梦中叫醒抓走。第二天,我们也被赶出家门,日本宪兵在我家大门上贴上封条,上面写着“敌产管理处封”。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是被列入“抗日分子”名单而被关进集中营的。
父亲被抓走后,起先被关在万隆市郊的监狱里,每隔两三个月家人还可以去探监。但一年后父亲便不知去向了,家里人十分着急,整天提心吊胆,怕有不测。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集中营的土著守兵,神神秘秘地来到我家,原来他是受我父亲暗中委托偷偷前来通风报信的。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去向。原来日本人准备把集中营里的华人都送往缅泰去修“死亡铁路”,而且已经被送到海口待命出发。那时,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海战中已经失势,海路已被盟军封锁,所以最后去不成了。这真是上天保佑,如果真去缅泰修“死亡铁路”,父亲即使不是死于苦役,也会在铁路修成后被枪杀灭口。去不成后,他们便被押返到芝麻墟镇集中营。那位土著守兵还偷偷地告诉我,如果想见到我的父亲,可以前往芝麻墟镇的某一条街边偷偷等候,太阳落山时就可以看到一支服完苦役后回集中营的队伍经过那里,但千万不要被日本兵发现,会没命的。
当时我才十多岁,决心要去看父亲一眼,便一人骑自行车到芝麻墟镇上的那条街。我躲在街边一家华人的小店铺里等待。快天黑时,我看到一支回集中营的服役队伍拖着极度疲乏的步伐慢慢地走过来,因为隔着玻璃窗看不清楚,便不由地跑出去,站在马路边仔细观望从眼前走过的每一个人。我终于发现了父亲,他也看到我了,我们俩四目相视,心里有千言万语但无法表述。这时,日本守兵发现了我,上来便给我两记大耳光。店老板看到情况危急,便急忙跑出来,一边假装对我训斥大骂,一边把我拽回店铺,就这样把我从日本兵的刺刀下救出来了。我终生忘不了那一次的遭遇和店老板的救命之恩。50年后,我到印度尼西亚参加学术研讨会,特意去了芝麻墟镇旧地重游,想对当年救过我命的店老板再次当面致谢。可惜,已经人去楼空。
在日军占领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度日如年,我们一家七八口人搬进一间小小的平房挤在一起住,靠变卖家里的剩余东西和亲友的接济,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我还在街边摆过小摊卖肥皂,尽量想办法贴补家用,减轻我母亲的负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父亲也从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了,我们全家得以重新团圆。这时,中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世界“五强”之一,过去趾高气扬的荷兰人现在见到中国人也都变得彬彬有礼了。我感到非常自豪,中国人已不再是“东亚病夫”,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
日本投降两天后,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盟军到印度尼西亚受降的是英国军队,荷兰殖民者成立荷印民政管理署,企图复辟旧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捍卫刚独立的共和国,这就是1945年爆发的“八月革命”。我参加了万隆中华红十字会的救护队,以实际行动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斗争。
万隆市恢复平静后,学校开始复课,我也怀着美好的憧憬踏入新建的万隆华侨中学(侨中)的大门,重新过起向往已久的学校生活。侨中的三年是我人生新的起点,为我今后要走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初步基础。学习之外,我喜欢各种体育锻炼,尤其是篮球,我是校队和市队的主力队员,经常参加各种比赛。这可以说是我三年高中生活中阳光的一面。
但在同一时期,我也深深为祖国的命运感到困惑,陷入极度的迷茫中。抗战胜利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我满以为祖国的复兴指日可待,谁知接踵而来的是滚滚乌云。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国内物价疯狂飞涨,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另一方面,内战爆发,国家重新陷入战火之中。当时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了解,我也没有机会接触进步组织和阅读革命书籍,所以我一度陷入彷徨苦闷中,不知前途在何方。
后来,我借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才知道在中国还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接着,我设法借到一些革命书籍,第一次看到《新民主主义论》时,我就认定祖国的命运只能寄托给中国共产党。我也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我热爱中华,也热爱我的第二故乡——印度尼西亚,我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生,同时,我也要为促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共同进步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也上街加入庆祝游行队伍,大家边唱歌,边高呼口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轰轰烈烈的场面。那一刻,我对祖国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充满憧憬,决心毕业后立即回国,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生。
人生道路的新起点
1950年侨中一毕业,我便怀着报效祖国的决心,报名参加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同学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当时国际局势很紧张,中国内地已被封锁,一般邮轮不通,只有香港的太古轮船公司还有货轮运货到天津。我们回国决心已定,便与太古轮船公司联系,坐上太古轮船公司2000多吨的旧货轮从雅加达启程,穿过台湾海峡封锁线,直达天津海河码头。
到达天津的当晚,时任市长黄敬亲自设宴招待。他告诉我们,台湾方面已派军舰准备在台湾海峡拦截我们,把我们押到台湾去。在获得这个情报后,大陆立即跟香港太古轮船公司进行交涉,要求改变航线,一定要保证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安全回到中国大陆。这时,我才想起船离开香港的第二天一早,确实有一架侦察机一直在尾随,低空盘旋在我们货轮的上空,看来是在跟踪我们船的行程。我们这才知道,能平安到达天津,靠的是人民政府的保护。我深深地感受到,过去被人称作“海外孤儿”的华侨,如今第一次得到祖国母亲的关怀与呵护时的温暖。
另一件事也让我感动不已。在天津住了几天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派专人把我们接到北京,准备参加全国高考。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后,我们都忙于卸行李,有一位穿短裤的中年干部也在忙着帮我们卸行李。那时正值盛暑,行李卸完后,有人才把满头大汗的那位中年干部介绍给我们,原来他就是中央侨委副主任廖承志同志,我内心无比感动:“啊,这就是新中国的干部呀!”
一踏上国土的这两件事令我终生难忘,也使我暗下决心,要为民族复兴大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我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东北大学化学系,后来东北大学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我也愿意毕业后当化学老师,培养祖国需要的化学人才。
但是人生并非一条直道,一个人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拐角而改变轨迹。第二年暑假,第二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来了,中央侨委让我作为侨委干部负责安排学生的住宿。此时,正好我父亲参加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华侨归国观光团抵达北京,侨委又让我参加接待工作。其间,我父亲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受鼓舞,决心把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家业卖掉,把资本带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在当时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投资公司,他是宣传委员。他还把在家乡早先买的70亩果园全部无偿献给国家,他的爱国行动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当我顺利完成侨委交代的任务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我回不去了。那时候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刚建交,很需要印度尼西亚语的翻译人才。于是,中央侨委建议我转学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新建立的印度尼西亚语专业。我早已树立这样的信念: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印度尼西亚是我的第二故乡,发展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就是我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二话没说便欣然答应了。就这样,我告别了化学专业,走进印度尼西亚语专业。从此,我的一生再也不能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发展分开了。
从语言教学进入文学文化研究
我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工作了几十年,献出了我的全部青春和精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教学外,我经常被借调承担接待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翻译工作。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时,我参加了翻译组的工作,一起把苏加诺慷慨激昂的演说全部录下翻译成中文,通过电台让全国人民当天听到。之后,我还参加了许多重要的翻译和接待工作。在实践中,我认识到要深化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除了语言作为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外,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史和交流史。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便开始着重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和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史,并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后扩展到东方文学的研究,参加并负责东方文学史有关书籍的编写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语系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亟须的翻译人才。我作为东语系的一位年轻教员,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放在专业语言的教学和翻译工作上。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东语系的年轻教师纷纷响应,但如何进行科研,大家心中没有数,不知从何做起。作为当时的系主任,季羡林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心得体会,有针对性地为东语系青年教师作了多次专题讲座。他的报告使我茅塞顿开,看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我一向对文学感兴趣,高中时就喜欢看中外的各种文学名著,所以,我决定以印度尼西亚文学为主攻方向。我开始学习文艺理论,拓宽文学文化的知识面,大量阅读印度尼西亚的文学论著和主要文学作品,一步一步地打好基础和积累知识,朝既定目标迈进。
季羡林教授是我国东方学的泰斗,培养了一大批东方语言、文学、文化的教学研究人才,我自己就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作为东语系的教师,我有幸得到季羡林的直接教导和指点,使我从单纯的语言教学逐步走上印尼—马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道路,后又逐步扩大到东南亚文学和整个东方文学的研究领域。
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季羡林负责东方文学的总编辑工作。东语系搞文学的教师大多参加并成了东方文学各分编委的主力和骨干,我自己也当了东南亚文学编写组的主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两年多的编写过程中,季羡林经常召开编委会,直接带领编委们共同讨论和研究有关东方文学条目的各种问题,使我对东方文学的认识和兴趣不断提高,并决心要把自己的专业文学研究与东方文学研究直接结合起来。
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积极筹备出版《外国文学简编》作为高校外国文学的基础教材。《外国文学简编》计划出“亚非部分”,在协商之后,当时便决定由朱维之、雷石榆老前辈和我担任主编,把全国15个高等院校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第一次集结在一起,共同编写我国第一部东方文学教程。整个编写过程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不但带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东方文学的研究队伍,同时也催生了我国第一个东方文学研究会。1983年,在乐山召开的最后定稿会上,大家决定成立高等院校东方文学研究会,我被选为副会长。
我还参加了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上下册的编写工作,并担任副主编。这部我国最大、最全和最权威的东方文学史巨著于1995年出版。为了大力促进我国东方文化研究的发展,季羡林进一步制定了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即编纂一套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东方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内容涵盖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计划出版500种,季羡林亲自担任总主编,我担任了东南亚文学相关书籍的主编。我负责和主编的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我完成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也被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于2003年出版,并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九三〇”事件。不久,中国与印尼两国便断交。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老师们不知今后该做什么,对前途感到茫然。但作为教研室主任的我没有丧失信心,因为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来看,我相信断交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们应该为以后复交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于是在1977年,我便建立词典组,把全部力量调动起来编写《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编成,于1989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有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88年,印度尼西亚举办第五届印度尼西亚语言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印度尼西亚官方五年举办一次的印度尼西亚语言最高的学术会议,邀请外国著名学者参加。我也收到了邀请,成为断交后第一位被邀请参加会议并作为大会学术报告人的中国学者。这次大会使我有机会与印度尼西亚学者、华裔社会人士直接接触和交流,同时更感受到语言和文化交流对双方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觉得有必要更加努力地培养印度尼西亚语人才与开展印度尼西亚文学文化和两国交流史的研究。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当初来北京筹办大使馆的印度尼西亚公使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想从我这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我给他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念,还带领他参观东南亚国家在北京开设的企业。后来他问我:“在两国断交期间,您是否继续教课和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文学、文化?”我说:“因为我相信两国断交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总会有复交的一天,所以我从没有停止过对印度尼西亚语的教学和研究,而且主编了《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并出版。”他听了很感动。后来,在把我介绍给复交后首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时,他特地说:“断交期间在中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那就是梁教授。”从此,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有重要的外事学术活动便经常邀请我参加,我也愿意为促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鉴于印度尼西亚语言发展很快,着眼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需要,我们继续编写更大、更全、更新的词典。经过数年奋斗,一部崭新的、大型的《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终于于2000年在雅加达出版,并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部长和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都拨冗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部大词典荣获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这期间,我与马来西亚的学术交流也增多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语言文化上是同一源流。1992年,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马来语言国际研讨会,并被指定为大会报告人之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学术论坛上。我用马来语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国的马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一次阐明马来语言在中马交流史上所起的作用。1994年,我被马来最高学府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要我在该校用马来语举办讲座,专门讲有关中马文化交流的历史,并邀请我用马来文写成一部专著,即《光辉的历史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关系》。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用马来文写的有关中马语言文化交流史的学术专著,由于引用了大量在马来学术界还鲜为人知的中国史料,受到马来西亚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深得好评。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科学地阐明中马友好关系的源流,借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以便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深彼此的友谊和信任。由于我在马来西亚的学术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果,2004年10月在北京庆祝中国—马来西亚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上,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亲自给我颁发了“马来西亚—中国友好人物荣誉奖”,以表彰我在语言、文学、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
进入21世纪,我虽已过古稀之年,但赤子之心未变,仍想为促进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继续发挥余热。其间,我编译了汉语—印度尼西亚语对照的《唐诗一百首》,于2005年8月在雅加达出版。接着,我继续编译了《宋词一百首》。能把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高峰——唐诗和宋词从原文直接翻译成印尼文介绍给印尼广大读者乃是我平生之夙愿。由于我在翻译工作上做出的成绩,中国翻译协会特授予我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我为促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2006年8月17日,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国庆61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特拉查特地给我颁发了“贡献奖”,表彰我为促进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北大新闻网还为此发表了专访报道,说我是“架设文化桥梁的民间大使”。

2006年,印尼大使向梁立基颁发“贡献奖”奖状,右三为梁立基
这些年我虽已退休在家,却仍在继续进行科研,集中精力搜集我国非常丰富的史料用于研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走向战略伙伴关系的整个历史进程,并继续积极参加国内外举办的有关学术研讨会,写了很多专题论文。为了让印度尼西亚学者和广大读者能更直接地了解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我集中全力,用印度尼西亚文撰写了一部专著《中国—印度尼西亚从朝贡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2000年的历史进程》,并于2012年在印度尼西亚正式出版,受到各界的重视。
如今我已入耄耋之年,不敢喊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样的豪言壮语,但却想起苏轼在《浣溪沙》里说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在经历了曲折漫长的道路之后,如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尤其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全面合作越来越紧密和广泛。我这个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老归国华侨,除了感到欢欣鼓舞之外,更多了一份历史的使命感。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继续为促进中国—印度尼西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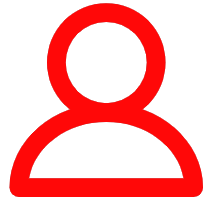


我要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全部评论 (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