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大学人丨刘永祥:“五四”的真意义:青年觉醒与大国转身
“敝会发端于 ‘五四运动’之后,为外交之声援,作政府之后盾,实寄托于国家主义精神之中。”
这是1919年5月18日《申报》所载《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报界函》中的一段文字,也是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最早使用“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文本。纵观几千年历史,似乎没有哪一场运动像“五四”这样如此迅速地被命名。更令人惊叹的是,短短几天后,五四精神也已开始被诠释。5月26日,《每周评论》上刊登了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表彰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的牺牲精神。此后百年间,五四运动的概念一直在沿用,而五四精神的内涵则日益丰富,“五四”意义的面相也如万花筒般让人眼花缭乱。纪念越多,意义反倒越模糊。关于“五四”,我们最该记住的,究竟是什么?
不管是五四运动的命名权,还是五四精神的解释权,最早都掌握在发起这场运动的学生手中,充分反映出他们的自觉意识。所以,一切均应从这个特殊的群体谈起,亦即青年觉醒。
觉醒的青年
中国古代的传统是重老轻少,少年老成常被赞许,年少轻狂则常遭诟病。这一伦理共识在晚清动荡时局下,逐渐被颠覆。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以少年中国取代老大帝国的宏愿。如果说梁启超笔下的“少年”只是新兴国族的隐喻,属于“想象的中国”范畴,陈独秀笔下的“青年”则不再是虚指,而是接受了新式教育、即将改变中国的社会阶层实体。至五四运动前,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至少已有几百万。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本就是继续梁启超的事业,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依稀仍带着“少年中国”的影子。文中如此歌颂青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尽管文章的发表和刊物的创办,都没有像陈独秀所期盼的那样引起巨大反响,但对青年的重视以及文中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已经预示了一场新思潮即将席卷全国,也预示着在经历过器物阶段和制度阶段后,救国的方式要转移到文化层面了。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它的内核并不是要消灭儒学,而是废弃礼教。与其说它是一场文化运动,不如说它是一场伦理革命。简单点说,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我们是新青年,我们要换一种活法。杨振声在《回忆五四》里的一段话就很典型:
“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

《新青年》创刊号
“新青年”三个字,其实划清了两条界限:一是与老年相对的青年,一是与旧青年相对的新青年。新与旧的问题,贯穿了整部中国近代史,越往后,越激进。激进,本就是青年人的特点。应该说,新文化运动让清末以来的新式教育上了一个台阶,没有这一次“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启蒙,也不会有后面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所以后来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把两者并称的概念,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烦闷的根源
问题在于,完满的人生观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形成,新青年们发现,急急忙忙砸碎了旧的牢笼,却没有新的体系可以凭借。民国初年的思想界出现了双重危机,传统文化自不待言,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而曾经完美的西方文化在一战后也遭遇了种种问题,“西方文明破产论”在青年中相当流行。因此,新文化运动确实带来了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让青年们发现了真正的“人”,但同时也由于新思潮内容过于庞杂,反倒让他们找不到重心而陷入处处都是问题的茫然无措。
“‘人’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自堕地到现在,都是昏昏董董,在梦昧里谋生活,什么人生观,都是莫明其妙。”“人心失其所信,竟无安身立命之方。”……类似的话语,在当时几乎俯拾即是。求解无门的结果,是很多青年选了自杀。陈独秀的《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青年人的烦闷,表面看是人生观的崩塌,实则还有别的根源,那就是国家的衰弱。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都一再提到,中国像一盘散沙。这是晚清以来国家衰落、传统被消解的必然结果,而每遭遇一次挫折,人们就越渴求新的“向心力”。看似被打倒的传统,总在不经意间规定着前进的方向。习惯了集体生活的国人猛然发现,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作为前提,所谓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根本无法带来归属感,反而更增强了“离心力”。皇朝、宗族已然被踩在脚下,迈出的步伐坚决不能回头,只能一路向前。于是,觉醒的青年们开始寻求新的集体化生活,组织的力量迅速凸显出来。
大国的转身
组织化和团体化并非五四运动所带来,清末以来即已呈现为一种趋势,只是这条路究竟对与不对,力量如何仍是未知。五四运动,就是最完美的试金石。一群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竟能逼迫政府就范,真令人大开眼界。这,无异于给组织化打了一剂强心针,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群体和组织的力量。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几百万人的全国大游行,除了强烈的爱国心之外,背后的各类组织实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更是极为关键的元素。青年们多年以来积压的烦闷得以宣泄,人生的意义似乎也不再缥缈。以组织为载体,个体生活和国家意志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所谓青年觉醒的背后,实在是组织觉醒。但是,哪些组织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并改变中国呢?这个时候,“主义”登场了。
“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丝毫不逊色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种救国思潮来得又快又猛。时人谓:“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才是拯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正确道路?”(《黄克诚自述》)不能只是提出问题,必须能够解决问题;不能只是解决某一方面问题,必须能够彻底解决所有问题。自从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以后,中国人形成了普遍的激进情绪,总想找到一种方案,迅速拯救中国,超越西方。三民主义在最初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与辛亥革命喊出的“毕其功于一役”口号密不可分,但它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国家制度,反倒让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在激进的语境中,不能迅速救中国的,很快就会被视为陈旧而遭遗弃。人们渴望一个带有综合性的,更先进的主义来拯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恰恰提供了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把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虽已表现出来,但尚未形成广泛的传播,因为这一先进理论的有效性还没有得到完全印证。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马克思主义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原因何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新模范国出现了,它就是——苏俄。短期内走向富强,是所有中国人所期盼的。“走俄国人的路”,遂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曾经被视为完美的西方国家,在一战后显得破败不堪,而且还在巴黎和会上无情地抛弃了中国。强烈的心理落差,使国人在经历转身向东学日本、转身向西学欧美后,再度迎来大国转身——向北学苏俄。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也不是某个群体的选择,而是整个国家的道路转变。
马克思主义成为潮流,新一次的大国转身正式起航。历史演进到这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极其自然。此后,“中国往何处去”这个近代以来的永恒话题,就有了明确的答案。从“新文化”(《新青年》)到“五四”再到中共成立,是一条十分清晰的历史逻辑链条。(作者:刘永祥,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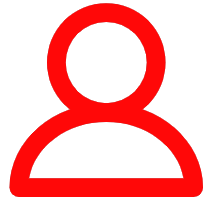


我要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全部评论 ( 条)